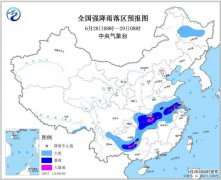春节前后,一连几夜,睡梦里全是故乡的年景、年味。
春节是一缸陈酿,被节令的咒符封存,在人们的殷殷期盼里,直到腊月才缓缓打开。当朔风扫净天空的阴霾,雪花浆洗了岁月的风尘,腊月的酒就再也封不住,香气四散,人们踏着厚厚的积雪回到故乡,畅快淋漓地去饮那坛岁月的醇香。
年味的香气就像一道岁月里的密码,折叠在二十四节气的夹缝中,尘封于十二月的窖缸底部,寒风凛冽的腊月,它被纷飞的大雪撩拨,封条瞬间风化。千里冰封也封不住的香气将基因里的密码激活,人们骚动不安,所有的指向都是一个方向:回家过年。
不在家乡过年已有三十个年头了,本想退休后回家乡足足地过上几个年,却因儿子们都在城里工作,大年三十才放假,老两口独自回家过年又怕他们担心,且多年不住的窑洞也需要整修清理,种种原因导致回家过年的念头胎死腹中,有时鼓足勇气想把它说出来,却又卡在喉咙里硬是将其卡死。没想到它并没有死,而是化成梦景,使我品足了家乡的年味。
老家在一个孤僻的山村里,那里没有城市的繁华和璀璨,但那里的清幽年味却留住永恒的农家淳朴的记忆和希冀的终也洗刷不掉的思念。
儿时的过年是盼来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马拉松式的吞糠咽菜,把胃胄困的魂牵梦绕,在极度的忍耐中等待着年三十的到来。因为不但有鞭炮放,新衣穿,更有好的吃。大年三十早上油糕粉汤,晚上猪肉羊肉粉鸡丸子,把人想得睡不着觉,涎水直往外流。而初一的头脑、饺子都由于除夕的海吃苦撑搞得痛若难咽了,但还要硬撑着多吃几口,因为过了这一天,就再没有好的吃了。本来腊月的天是最短的,但从腊月初一就开始盼望,随着年关的越来越近,感觉中的日子却越来越长。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一天,却一恍而过。那时经常在想,为什么就不能多过几个年,让自己过足了再回到平常。因为从初二开始就将年夜饭的剩余全部封冻起来,等待正月里请人的那一天供请来的客人吃,当然自己也能再次趁机饱餐一顿。那时总想如果把日子定格在过年上该有多幸福。有几次想着想着让诱惑力彻底摧毁了忍耐力,而寄盼的彻夜未眠。
长大后求学工作,离开了家乡。家或许因为偏僻依旧贫穷,因为贫穷才会出走。但那根线永在,那是根,是安放灵魂的地方。回家过年是一年一次的灵魂皈依,一年一次的状态还原。一年的苦钻和打拼,城里的喧嚣和忙碌,让心变得坚硬无比,许多想念冰封在心底,许多感念来不及梳理,就那样杂七杂八地存放着。一旦过年将所有的这些杂乱无章带到踏实的土炕上,就不再是懵懂的混沌了,都变的清晰和振作起来。原来,一年的辛劳,需要一个家乡的甜美香梦来养足精神;一年的疲惫需要一碗家乡的黄酒来再次壮起行囊;一年的隐忍和伪装,吞下的苦辣,咽下的酸咸,需要在家乡的酒杯中慢慢软化。攥一把家乡的柴火,骨头就更硬气;吸一口村口风,打拼就更有劲;喝几天家乡的美酒,所有外面沾染的浊气就荡涤干净。在祖坟上烧一刀麻纸,放一窜鞭炮,闯外的儿孙回来了。不管在外面受过多少风寒,摔过多少跟头,回到故乡的土地上,爷们都是掷地有声。
回家的路其实并不遥远,中间没有万水千山,但却横亘着沧桑岁月;回家的路或许也不很近,需要用一年的盼望捻成一张票根。车站、渡口到处是拥挤的人群,各种各样的启程和出发,充满了隆重的仪式感。积攒久远的豪迈情怀,伴随着漫天飞雪进入高亢的乐章,患得患失的心情,焦灼不安的面孔,都为一张回家的票。回家的人摩肩接踵,回家的路一票难求,腊月最动人的一句话是:有票了!手握一张回家的票,那才是握住了最大的幸福。大寒小寒又一年,腊月的风雪分外殷勤,来给年的盛宴加油助兴,回家过年的人,头顶雪花,身披尘埃,日夜兼程,朝圣般浩浩荡荡向着乡关进发。大雪封路,坐船也要回家。
回家,是腊月里最闪亮的主题。家里有什么呢?破旧的屋子,衰老的父亲,辛劳的妻子,以及两个可怜巴巴的儿子,被寒冷覆盖,跟简陋相依。他(她)们期盼着自己带给温暖,带给理解,带给过年的欢乐!还有老家的两扇柴门,当初是自己一甩门扬长而去,现在只有回去,深情地给当年那一声“吱呀”的哀叹忏悔。
汽车、木船都坐过了,最后需要用脚板去丈量那崎岖的山路。这仿佛是自己欠故乡的一笔债,一回到这片土地上,那亏欠过土地劳作和汗水的脚就会踩出水疱,疼痛难忍。
远远望见家乡的大榆树,更显沧桑,它是村庄的年轮,枝丫上还刻着游子的童年故事。走着走着看见几缕炊烟,泪就盈满眼眶,这时才想起自己已有一年没有回家了,深感自己是不孝的儿子,不称职的丈夫和最没资格的爸爸。是自己让他(她)们吃尽了苦头,想着想着泪水突眶而出,潸潸而下。回家后才知家人盼望的心情比自己还要急切。几天来从早到晚老瞅着圪洞口头出现奇迹,期盼之情无人理解。
后来村里的一位哥哥终于当上了农产公司的经理,家乡也通了公路,至此,回家再无难事。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年货一年比一年丰盛,大包小包一大堆,所有年货一应俱全。从腊月二十三到家里,磨豆腐、碾米、压面,直到年三十全家人面对从未有过的丰盛,把年味推向了极致。正月初二开始,在外工作的二、三十人轮流被村里人请去吃饭,一家吃罢再一家。一锅红茶,几桌凉菜,围着方桌席炕而坐,张长李短、东丰西欠、交流收获、分享苦乐、边说边饮、边喝边叙,白酒喝醉,红茶饮醒,家乡的年味如此浓烈、如此深情、如此醇香、如此迷人,浓浓的年味浓浓的情,父老乡亲乐融融。直到小年过后,才返回工作岗位。
再后来,为儿子上学,将家人接到县城,从此再没有回家过年。城里的年,项目繁多,规模庞大,热闹非凡,无论视觉、味觉都堪称盛宴,与家乡无法相比。但对我而言,却总也找不到家乡的那种年味了。每当夜深人静独对星空时,浮华和名利都被过滤掉,心灵惦记的还是最初那两扇门,那是故乡的眼睛,铁锁锁不住它牵挂的眼睑。当初,两扇门“咣当”一声落锁,院子里的枣树也咿呀,树上的麻雀也嗟叹,一户空荡荡的门扉,追着打问号的乡路问:你要到何处去?
再后来因工作调动,举家搬到市城。市城比县城过年更热闹,但自己觉得离家更远了,心灵更加孤独。睡梦中手扶家乡的柴门沉思,门板也是游走的游子,却总也走不出门框制定的距离。门框是门板的摇篮,用上下两个门臼,拴住了门板那浪荡的心。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那把锁思念钥匙和打开它的手,思念都结痂成黄澄澄的铁锈;那门槛寂寞地思念迈进迈出的脚步,思念得生出许多苔藓。故乡的山水、院外的大榆树和院内的小枣树、小桃树都在惆怅的思念中等待,多少年多少个月圆之夜的皎洁月光,都在老锁喑哑的喉咙里。那两扇门板很旧很老了,好像松动的牙齿,说不定啥时候就卸任了;又像渐渐失去了力气抓不住什么的双手,要不了什么因由就撒手了。那门终究会破损倒塌,护不住一个荒芜庭院的旧闻和记忆,背着那扇柴门行走的我,终于明白,自己倾尽一生,都走不出家门的凝望。正在悲伤处,屋里一声巨响,将梦中的我震醒,原来是老伴放了一个开门炮。这时才发现自己已泪流满面,一翻身又感觉枕巾也湿透了。
责任编辑:张伟
- 沈明志:让历史告诉未来2018-09-03